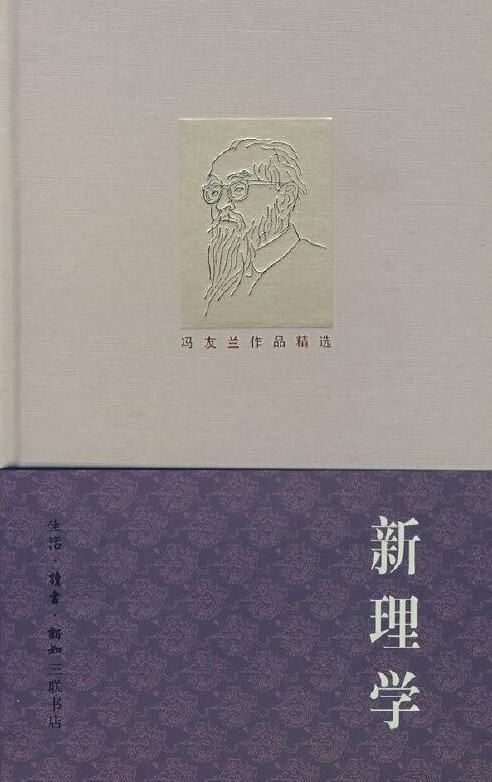牟宗三批評馮友蘭的新理學是妄人妄作,接續不到宋明理學的問題意識 (<客觀的了解與中國文化之再造>),但細究新理學創建的發生歷程,馮氏未嘗不懷有一番苦心。
新理學成立於抗戰期間,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在此之前,維也納學派大盛,不少中國學人亦受其影響,包括胡適。胡適的學生傅斯年,曾說「德國哲學只是一些德國語言的惡習慣」,將德國的形上學視作錯用德語的結果,將之解消,傅氏顯然深受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論影響,弟子影響老師,胡適後來索性「不看西洋哲學書」,連「哲學史」都改稱「思想史」,更一度呼籲「哲學關門」(王汎森<從哲學史到思想史 – 胡適的英文《中國思想史大綱》草稿>)
胡適 1917 年到北京大學當教授時,馮友蘭是三年級學生,胡比馮大四歲。對於老師激烈的立場,馮氏不以為然,他不是要全盤否定維也納學派對傳統形上學的批判,只是在傳統形上學以外,還有沒有另一種建構形上學的可能,誠如胡軍所言,馮友蘭接受邏輯實證主義的方法,自覺地承擔起重建形上學的任務,「新理學的工作,是要經過維也納學派的經驗主義而重新建立形上學。」(<馮友蘭《新理學》方法論批判>) 假如成功,哲學自然也不用關門了。
新理學的概念和命題,清一色是抽象原理與普遍概念,以形式邏輯語言表出之,不涉及具體科學領域中的真實知識,如「凡事物必都是甚麼事物。是甚麼事物,必都是某種事物。某種事物是某種事物,必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事物必都存在。存在底事物必都能存在。能存在的事物必都有其所有以能存在者」之類。馮氏自信如此建立新形上學,定能剔除傳統形上學的不足,免於維也納學派的批評。
馮友蘭的嘗試成功與否,眾說紛紜。要之,馮氏以外,金岳霖、張岱年皆堅持運用語言分析方法建構形上學,以形上學為哲學的核心部份、揚棄邏輯實證論,彷彿是三、四十年代中國大陸哲學界的主流。
當代新儒家建構道德形上學,他們也是在尋找另一種建構形上學的可能。不過,其對邏輯實證論、語言分析有保留,此在牟宗三以下一番話便可窺見:
我並不反對分析,而且我也贊成人人都該有一些這種訓練,但不能只宣傳分析、崇拜分析。分析是一種工作,是要作的,是要討論問題、分析問題的……英國人有這種傳統,能夠分析,而且很精緻細密,這代表英國人的性格。這種分析的路數,我給它個名稱叫「纖巧」。一方面從好處說,它確是精巧。這就好像細刀刻木,刻久了的確很細緻,但不小心一碰就碎了、沒有了。所以在另一方面,一成纖巧就出毛病……分析哲學的學者雖說分析只是個方法,不代表任何主張,但事實上它就是個主張……因此往往分析的結果不是歪曲原意,就是把問題分析掉了。他們通常分析黑格爾的幾句話,以黑格爾的話為譏諷的對象。但黑格爾的話是否真的無意義呢?這種態度就不對,不先作客觀的瞭解,反而先斷定人家無意義,把自己主觀的不瞭解當成客觀的無意義,這根本就是「不邏輯的」(illogical),根本就不是「分解的」(analytic)……要恰當的瞭解就需要徹底的分析,但不能將問題分析掉。(《中國哲學十九講》)
胡、傅以語言及邏輯分析解消形上學,走得最極端。馮友蘭以語言及邏輯分析重建形上學,立場較溫和,但仍偏近英美路子。至唐、牟,從客觀了解康德「道德形上學」、黑格爾「絕對精神」重建形上學,這已是另闢蹊徑。
置於此一歷史脈絡下,馮友蘭不屬於當代新儒家陣營,是非常清楚的。
而由於新理學是有意識地回應維也納學派的挑戰,其理論得失當據「其命題及概念能否順利避開維也納學派的可能攻擊」而定,而非據「其命題及概念能否遙接程朱理學乃至宋明理學的問題意識」而定。事實上,新理學分明是馮友蘭個人的哲學創造,他僅用伊川、朱子的文字話語講自己的新實在論思想,故云「舊瓶裝新酒」、「接著」講而非「照著」講。純以新理學不契於程朱哲學乃至宋明儒之宗旨,遂謂新理學是妄人妄作,此未免對馮氏的苦心孤詣不了解,亦難以對新理學有一客觀公允的評價。
胡軍說:
如果囿於馮友蘭「接著」宋明理學來講《新理學》的思路,我們就將不可能完全正確地理解《新理學》一書的哲學性質。
但他同時指出:
綜合命題的特徵在於它對經驗事實有所述、有所傳達,它的真假完全取決於是否與相應的事實符合。但馮友蘭的形上學命題是對於事實作形式的解釋的命題……這樣的命題看似綜合命題,實則不然。它們根本就未向我們提供任何有關經驗事實的信息,所以它既不能被經驗事實證實,也不能被經驗事實證偽。
……《新理學》中的四組命題,按照馮友蘭的看法,它們既是重言式命題或分析命題,也是綜合命題。但我們卻認為,它們既不是重言式命題或分析命題,也不是綜合命題。所以,這樣的命題是不能擔保《新理學》一書中的形上學的真值的。(<馮友蘭《新理學》方法論批判>)
竊以為這是對馮氏新理學較中肯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