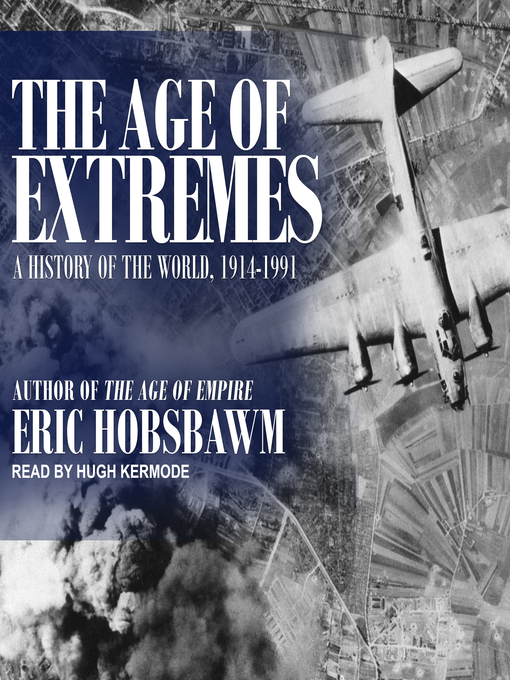余英時說香港自由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已得到強化和深化,不易被政治暴力摧毀,我是不認同的。我反而較接受李怡的比喻「你做個瓷器,做得好要很多功夫,但你打破就很容易,用手掃一掃它就碎了。」由 2014 至現在,九年時間,香港已被收緊到連六四集會都舉行不到,最近更有傳立廿三條,「不犯法不代表不破壞國安」,意味著他朝國安機構可向不犯法的唱衰中國和香港的異見者下手,回望余先生的意見,他看得實在太樂觀。
另外,歷經三年疫情及《港區國安法》,香港人已變得敢怒而不敢言,激烈抗爭幾乎消失。仍嚮往自由的,選擇到台灣、英國、加拿大去,原有的香港族群實際等於花果飄零。刻下距離 2019 不遠,大家在外還會說心繫香港,就香港各項議題發聲,但一年、兩年乃至十年、二十年後呢?記憶與遺忘,只怕仍是遺忘勝一籌,即使不遺忘,香港亦只怕成為各海外 KOL 的談資,賺錢討個生活的工具而已。以為香港人會持續激烈的反抗,這無疑脫離現實。
至於共黨內外有人提出民主訴求,六四後難道沒有嗎?動輒監聽、禁聲、恫嚇家人,有訴求亦無法轉成具體行動。至於依靠西方國家,近日英國辛偉誠拒關孔子學院,被指親共。台灣對港人移民亦擬加辣。考慮及自身本國的利益,誰願意長期與中共為敵?批評是一時,覺得西方批評香港就有救,太異想天開。
誠然,余英時先生視香港為他一個故鄉,他對這個彈丸之地有情,故不忍見它沉淪。可是,客觀形勢是昔日香港已一去不返,此乃不為人的主觀意志而轉移,認清事實或許比抱有無限幻想更佳。
關於余英時的學術定位問題,亦值得一講,有謂他繼承錢穆,更多指他和胡適一脈相承。這裡需要指出,余先生的本行是治中國史,曾得到錢穆先生親炙受業,兼推薦跟從楊聯陞讀博士。他撰《中國知識階層史論》、《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都帶有通貫數個朝代的眼光,是某種意義上的通史,《方以智晚節考》更得錢先生推許,他的學問怎會是胡適一派?胡適、傅斯年相當注意史料的真偽,余先生很少相關著作,更見他和胡、傅非同路人。
余英時和錢穆不同,一是他不寫大部頭通史,而傾向專題研究,以小見大。二是他喜歡援引西方理論詮解中國史,如以柯靈烏對比章學誠,用心理史學解構宋孝宗晚年用人部署,都是其中例子。這是余氏治學的獨特處,和胡適無干也。
余英時和胡適有契合,就只在於政治上二人皆理解並且認同民主自由的價值,在文化上非一面倒吹捧中國傳統。余英時對憲政民主制衡統治者權力,是首肯的,錢穆覺得這是造成統治者和人民的矛盾對立,社會不和諧。另余英時認為,儒家文化可在多元社會中被包容,兼且發揮正面作用,錢穆則覺得爭取自由民主不如提倡儒家的修身成德。
總括而言,余英時的學問傳承自錢穆,此乃無容置疑。他和胡適更多是「英雄所見略同」的思想上的同路人,同歸宗於自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