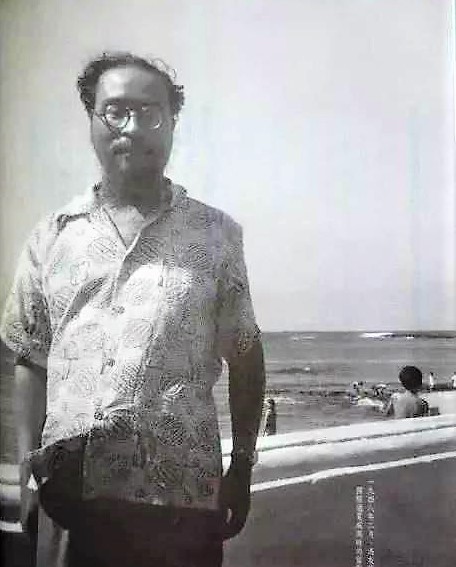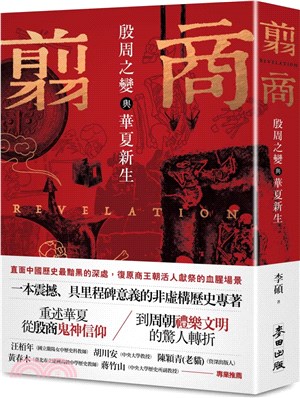金春峰是馮友蘭的學生,在《馮友蘭哲學生命歷程》中,他援引史料剖析了馮氏留在大陸的心路歷程。
馮友蘭在解放前一直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任客座教授,講中國哲學史。然而,他不打算長居美國:
我在國外講些中國的舊東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館裡面的陳列品了,心裡很不是滋味。當時我想,還是得把自己的國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樓賦》裡的兩句話:「雖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到 1947 年,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南京政權搖搖欲墜,眼看全國就快解放了,有些朋友勸我在美國長期住下去。我說:俄國革命以後,有些俄國人跑到中國居留,稱為「白俄」。我決不當「白華」。解放軍越是勝利,我越是要趕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國解放了,中美交通斷絕。於是我辭謝了當時有些地方的邀請,只在回國途中在夏威夷大學呆了一學期。
這段文字收錄於《三松堂自序》,《三松堂自序》是馮友蘭晚年的回憶錄,上述所記當為馮氏心底話。
除了國外的不快經歷,思想上馮氏亦慢慢向馬克思主義靠攏。《新事論》一書明確表示:
(1) 舊的家庭本位生產方式應該結束,代之以資本主義以近代工業為基礎、社會為本位的生產方式。這是歷史的進步與必然。
(2) 不論共產黨或國民黨當權,中國都要走上現代化。而社會主義式的社會本位的中國現代化,比資本主義式的現代化更好,更少弊病。
(3) 文化道德上,儒家文化所集中體現的家庭本位觀念,隨著社會走向現代化,理應退出歷史舞臺而由新的道德觀念取而代之。社會主義的道德以「尚賢」、「大公」、「無私」為基礎,不僅比傳統道德優越,比資本主義道德與文化也更高。
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及社會主義的同情乃至接受,令他未有對舊文化、舊道德之淪喪感到焦慮,也未有對信奉新思想感困難,此令他對共產黨不生厭惡。
和當時多數知識分子一樣,馮友蘭對國民黨大失所望。1945 年 4 月,馮氏被國民黨河南省黨員代表大會選舉為出席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但他 4 月 26 日向朱自清等談代表大會情況時,卻說:「余等大失所望。老頭子 (指蔣介石) 毫無遠見,彼全然背棄自己之信念,遲早將引起反抗。」
1945 年 6 月,馮氏撰文指封建社會的本質如不改變,所有政治的改變都是空的,不過是一種表面的裝飾。文中主張徹底實行「平均地權」的土地政策,剷除舊社會中的特權階級,使舊社會中不勞而獲的人,必須工作才能吃飯。社會中的人都立於平等的地位,真正的民主方可實現。「平均地權」是孫中山先生提出,但孫不講地主與農民之間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不從廢除「不勞而獲」與封建特權立論。馮氏的提法,更接近共產黨的主張。
同年 11 月 25 日,昆明大中學生舉行反內戰大會,26 日罷課,要求政府取消集會遊行禁令,保障議論自由,懲辦肇事者,停止內戰。國民黨對學生集會實行鎮壓。馮友蘭與聞一多等起草抗議書,向報界發表。馮氏態度雖不是左派,但亦非站到親國民黨一面,屬第三勢力。隨著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馮氏更加同情共產黨。
馮友蘭夫人的二姐任芝明參加了共產黨,《三松堂自序》有這麼一段:
我回到北京以後,叔明告訴我,他的二姐任銳曾經隨著延安的軍調代表來到北京,也到過我們家;二姐說:「你們可以到延安去,現在延安、北京之間,常有飛機來往,如果你們決定去,全家都可以坐飛機去。」叔明說,二姐已經走了,走的時候交代說:「你們什麼時候決定了,可以去找葉劍英同志去。」
延安釋出隨時歡迎參加革命的訊息,令馮友蘭覺得再沒有走的必要:
當時我們商量,作出了一個決定,反正我們是不走的,解放軍也快要打到北京了,我們就在這裡等著他們吧。當時我的態度是,無論什麼黨派當權,只要它能把中國治理好,我都擁護……當時在知識份子中間,對於走不走的問題,議論紛紛。我的主意拿定以後,心裡倒覺得很平靜,靜等著事態的發展……「何必走呢?共產黨當了權,也是要建設中國的,知識份子還是有用的……」當時我心裡想的,還是社會主義「尚賢」那一套。
他萬萬沒想到自己坦然自信地留了下來,竟是高估了自己與共產黨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