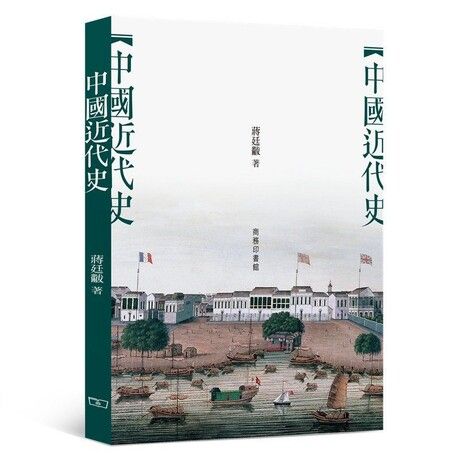蔣廷黻 1895 年生於湖南邵陽一個商人家庭。1912 年赴美國留學,1914 年考入俄亥俄州歐伯林學院,主修歷史,1918 年畢業後,旋即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專攻歷史,1923 年獲博士學位。
蔣廷黻未幾回國,到天津南開大學任西洋史教授。他與梁啟超堪稱南開大學史學系的奠基者,執教長達六年之久。1929 年 5 月,受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邀請,到清華大學歷史系任系主任。羅家倫也是哥大校友,二人在求學時期已結識,經常討論中國史學和研究方法的問題。蔣同時收集中國近代外交史料,並展開相關研究工作,其更率先講授中國近代外交問題,為中國近代外交史學科的奠立作出重要貢獻。
「九一八事變」後,蔣廷黻與胡適等共同創辦《獨立評論》,引起國民政府高層關注。1935 年,蔣棄學從政,加入國民政府,任行政院政務處長。及後專責協助國民政府處理外交事務。1965 年 10 月在紐約去世。
《中國近代史》寫於 1938 年,篇幅不多,僅五萬餘字,卻深入淺出地探討中國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
書中「總論」率先指出:
到了十九世紀西方的世界已經具備了所謂近代文化。而東方的世界則仍滯留於中古,我們是落伍了!
在談到鴉片戰爭的失敗時,蔣氏不諱言:
鴉片戰爭的失敗的根本理由是我們的落伍。我們的軍器和軍隊是中古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們的人民,連士大夫階級在內,是中古的人民。我們雖拚命抵抗終歸失敗,那是自然的,逃不脫的。
中國要擺脫積弱困境,抵抗帝國主義侵略,必須盡快實現近代化。實現近代化,具體言之,便是學習西方的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他說:
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並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俄國、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說的那個樣子。這三國接受了近代的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於是復興了,富強了。
本來鴉片戰爭軍事失敗後,就應該深切反省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可惜咸豐一朝清廷依舊妄自尊大,直至英法聯軍入北京,少數人才有所覺悟,知道非學西洋不可。中華民族因此喪失了二十年寶貴光陰。
在論洪秀全時,蔣廷黻提出了「歷史循環套」:
中國歷史還有一個循環套。每朝的開國君主及元勳大部分起自民間,自奉極薄,心目中的奢侈標準是很低的,而且比較能體恤民間的痛苦,辦事亦比較認真,這是內政倡明吏治澄清的時代。後來慢慢的統治階級的欲望提高,奢侈標準隨之提高,因之官吏的貪污亦大大的長進。並且舊社會裡,政界是才子惟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會裡,有志之士除作官以外,可以經營工商業,可以行醫,可以作新聞記者,大學教授,科學家,發明家,探險家,音樂家,美術家,工程師,而都名利兩全,其所得往往還在大官之上……總而言之,在中國舊日的社會裡,有心事業者集中於政界,專心利祿者也都擠在官場裡。結果是每個衙門的人員永在加增之中,而衙門的數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個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加增很多,民生痛苦的時候,官吏加多,每個官吏的貪污更加厲害,人民所受的壓榨也更加嚴重。
清朝到了嘉慶、道光年間,已處於循環套的最低點。內亂無日無之,最初有湖北、四川、陝西三省白蓮教徒的叛亂,後有西北回教徒之亂,西南苗傜之亂,同時東南沿海海盜猖獗。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正是那個時代和那種環境的產物。
蔣氏分析太平軍早期何以勢如破竹:
主要原因不是太平軍本身的優點。論組織訓練,太平軍很平常,論軍器,太平軍尚不及官軍,論將才,太平軍始終沒有出過大將。太平軍在此時期內所以能得勝,全因為它是一種新興的勢力,富有朝氣,能拼命,能犧牲。官軍不但暮氣很重,簡直腐化不成軍了。當時的官軍有兩種,即八旗和綠營。八旗的戰鬥力隨著滿人的漢化,文弱化而喪失了。所以在乾隆嘉慶年間,清朝用綠營的時候已逐漸加多,用八旗的時候已逐漸減少。到了道光咸豐年間,綠營已經成了清廷的主力軍隊,其腐化程度正與一般政界相等。土兵的餉額甚低,又為官長剝削,所以自謀生計,把當兵作為一種副業而已。沒有紀律,沒有操練,害民有餘,打仗則簡直談不到。並且將官之間,猜忌甚深,彼此絕不合作。
值得注意是「餉額甚低」,此在曾國藩組建湘軍時即有所改善,湘軍戰鬥力因此較綠營為高。
當時綠營之所以不能打仗,原故雖多,其中之一是待遇太薄。曾氏在起始辦團練的時候,就決定每月陸勇發餉四兩二錢,水勇發三兩六錢,比綠營的餉額加一倍。湘軍在待遇上享有特殊權利。
另外,曾國藩治軍也有獨特的一套:
曾國藩治兵的第一個特別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遺教是我民族的至寶。洪秀全既然要廢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敵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敵人……
……他是孔孟的忠實信徒,他所選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實同志,他是軍隊的主帥,同時也是兵士的導師。所以湘軍是個有主義的軍隊。其實精神教育是曾國藩終身事業的基礎,也是他在我國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別。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義。他覺得政治的改革必須先有精神的改革。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門下者,皆比較正派,足見其感化力之大。
曾國藩不但利用中國的舊禮教作軍隊的精神基礎,而且利用宗族觀念和鄉土觀念來加強軍隊的團結力。他選的官佐幾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鄉人。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這樣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別濃厚。這是湘軍的第二特點。
……曾國藩雖注重為人,並不忽略作事……湘軍作戰區域是長江沿岸各省。在此區域內水上的優勢很能決定陸上的優勢。所以曾國藩自始就注重水師。關於軍器,曾氏雖常說打仗在人不在器,然而他對軍器的製造,尤其對於大炮的製造,是很費苦心的。他用盡心力去羅致當時的技術人才。他對於兵士的操練也十分認真。他自己常去督察檢閱。他不寬縱他的軍官,也不要軍官寬縱他的部下。
在介紹甲午之戰時,蔣氏提及李鴻章和左宗棠關於「海防與塞防之爭」。
李鴻章在日本明治維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國的勁敵。他並且知道中國的勝負要看哪一國的新軍備進步的快。他特別注重海軍,因為日本必須先在海上得勝,然後能進攻大陸。所以他反對左宗棠以武力收復新疆,反對為伊犁問題與俄國開戰,反對為越南問題與法國打仗。他要把這些戰費都省下來作為擴充海軍之用。他的眼光遠在一般人之上。
甲午戰敗,原因在於:
第一,戰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艦隊排「人」字陣勢,由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居先,稱戰鬥之主力。海軍提督丁汝昌以定遠為坐艦,艦長是劉步蟾。丁本是騎兵的軍官,不懂海軍。他為人忠厚,頗有氣節,李鴻章靠他不過作精神上的領導而已。劉步蟾是英國海軍學校畢業的學生,學科的成績確是上等的。而且頗識莎士比亞的戲劇,頗有所謂儒將的風度。丁自認不如劉,所以實際是劉作總指揮。等到兩軍相望的時候,劉忽下令把「人」字陣完全倒置,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居後,兩翼的弱小船隻反居先。劉實膽怯,倒置的原故想圖自全。這樣一來陣線亂了,小船的人員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機先攻我們的弱點了。
其次,我們的戰術也不及人。當時在定遠船上的總炮手英人泰樂爾 (Tyler) 看見劉步蟾變更陣勢,知道形勢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遠就放炮,不要亂放炮,因為船上炮彈不多,必命中而後放。吩咐好了以後,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邊,準備幫丁提督指揮。但丁不懂英文泰樂爾不懂中文,兩人只好比手勢交談。不久炮手即開火,而第一炮就誤中自己的望台,丁受重傷,全戰不再指揮,泰樂爾亦受輕傷。日本炮彈的準確遠在我們的之上,結果,我海軍損失過重,不敢再在海上與日人交鋒。日人把握海權,陸軍輸送得行動自由,我方必須繞道山海關。其實海軍失敗以後,大事就去了。陸軍之敗更甚於海軍。
書中還有許多精彩的段落,留待讀者們發掘。最後,誠如馬勇所言:「蔣廷黻的這部『大家小書』,真的應了古人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的老話,他並非刻意經營的一本小冊子卻奠定中國近代史一個全新敍事框架。」